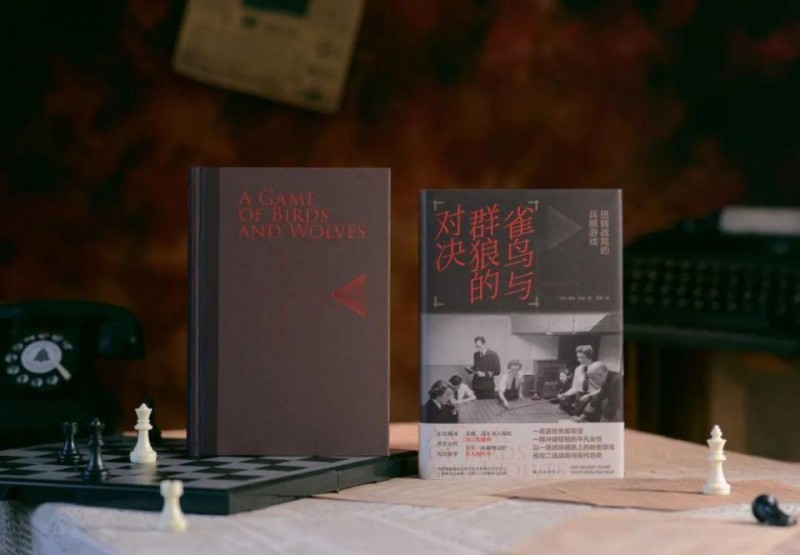“文学界有伟大的老女人吗?还是只有伟大的老男人?我想我应该准备好成为英国文学界的伟大的老女人。”在伍尔夫生命的最后几年里,她对友人如此说道。
“伟大的老女人”有多重意味。在此之前的知名近现代女作家少有长寿的,简·奥斯丁活到41岁,夏洛特·勃朗蒂38岁,艾米莉·勃朗蒂30岁……此外,伍尔夫这里所说的伟大,并不单指文学成就,她的意思是她将面向公众,发挥自己的“公共性”。
除了《一间自己的房间》这种原本就是面向女性的演讲改写成的作品,伍尔夫的“女性意识”在她后期的公共发声里俯拾皆是。1938年的《三枚旧金币》里,她设想了一种“漠然”策略。她认为所有的女性都是局外人(outsider),而作为局外人,应当漠视男性的好辩、自大,尤其是对战争的狂热,后者在第二次世界爆发前的欧洲背景下并不突兀:
“我们的国家”在她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都把我当奴隶对待;它剥夺了我受教育的权利,也剥夺了我拥有它的权利…… 所以,如果您坚持说你们作战是为了保护我,或“我们的”国家,还是让我们冷静地、理智地说清楚:你们是为了满足我无法共有的性别天性而战;你们是为了获得我不曾并且将来也不可能共享的利益而战……
从事后的角度看,她在“二战”期间反对战争是怪异的(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是犹太人,两人甚至都出现在希姆莱要即刻逮捕的人员名单上),也是逆时代潮流的(《至暗时刻》展现了当时英国政治中主战派与主“和”派的斗争,最后是以丘吉尔为代表的主战派胜出),但她敏锐地看到战争中的父权制因素,不得不说是超前的思想。
1931年,她在女性服务协会发表了一次演说,她提醒女性,即使已经成为职业女性,找到自我的任务也依然艰巨。她们的价值、梦想、情感,始终可能遭遇嘲讽。她犀利地指出,女人总在接受一套与自己的价值观多少有些偏离的价值体系。这些观点很难不让今天的女性深深共鸣。这些想法比《一间自己的房间》里对女性要获得经济独立的强调,走得更深。女性,不单单是智力发展被压抑,无法享有与男性相同的教育权利与发挥才能的权利;身为女性,更是一种本质性的处境。伍尔夫这时关心的是,女人,或者用今天的话说女性气质/特征,究竟是什么,以及这种特质能为文明做出什么样的贡献。
她意识到,最严峻的斗争不是与外部的斗争,而是与自己、与根深蒂固的让女性贬低自我的观念的斗争。对此,她本人就感受至深,1919年,已经出版了《达洛维夫人》的伍尔夫在《夜与日》出版前夕还在信中写道:“我能忍受阅读自己出版的作品,而不脸红、不发抖、不想躲起来的那个时刻,到来了吗?” 几乎每一部作品的出版都伴随这样的自卑情绪。
如果你主要是从《一间自己的房间》了解伍尔夫“女性主义”的一面,那么最新出版的林德尔·戈登《弗吉尼亚·伍尔夫传》中译本就会带来许多“惊喜”。除了上述伍尔夫晚年的转变,传记也囊括了伍尔夫复杂的女性主义面向及其 “前世今生”。
她复杂的性别意识和观念,其来有自。她的母亲是最早的职业护士,经常离开家去照顾病人,但同时也曾参与反对女性投票权的运动。她的父亲全力支持妻子的事业,他痛恨女人的智力被浪费,所以让凡妮莎学画画,让伍尔夫学习希腊文,却仍然认为女性不应该进入学校接受教育,还会对发表批判性言论的小说家奥利弗·施赖纳愤怒不已。伍尔夫不得不在家中接受教育,可是她却坐拥父亲庞大的藏书,能够尽情阅读。她一段时间的家庭教师珍妮特·凯斯,是第一批从剑桥大学毕业的女性,尽管伍尔夫非常珍视她,但在后者争取女性选举权的活动中,伍尔夫所做的只是帮忙给信封封口。伍尔夫像历代伟大的男作家、男哲学家一样,读了大量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,可是在她二十几岁沉浸于大部头经典的世界时,她仍有这样的困惑:“我,作为一个女人,有什么权利去阅读这些男人们写的东西?”
戈登告诉我们,尽管伍尔夫在写更为激进的《三枚旧金币》时,前所未有地肯定自身的力量,认为自己已经摆脱了所有的伪装,而且这部檄文式的作品出版后反响异常强烈,但这部作品却没有得到她周边亲友的理解。伦纳德、凯恩斯、薇塔,包括她的小辈昆汀·贝尔,都对这部作品不以为然。但也许她早就做好了准备,她在更早时便告诫女性 ,要“保持耐心,保持愉悦”。
伍尔夫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雷切尔·温雷克(《远航》)、凯瑟琳·希尔伯里(《夜与日》)、达洛维夫人、拉姆齐夫人(《到灯塔去》)、罗达(《海浪》)等,都不是从事社会活动的女权主义者,她探索的是平凡的,或者是困惑的女性。在她早期的《琼·马丁小姐的日记》里,她就开始关注作为匿名者、默默无闻者的女性。她把建立英格兰的祖先想象成一群无名无姓的女人,而英格兰的未来也建立在她们的梦想之上。
这种性别观和伍尔夫“反”历史、反英雄主义的历史观,是相关联的。在她那个时代之前的历史,往往是统治史,记录着战争、政权的更迭等“大事”,在这样的历史里,毫无疑问很难见到女性的身影。伍尔夫设想的历史,是要以创造性的家庭生活为核心,去关注那些日常的、微不足道的事物,关注普通人不为人知的想法和感受。对她来说,虚构小说就是历史,一种她所主张的新历史。

在虚构小说是历史的意义上,戈登还在伍尔夫的小说里看到了她的传记热情。戈登在这里指的并不是伍尔夫的传记体裁的作品,如画家传记《罗杰·弗莱》,或是仿传记体的《奥兰多》和《弗勒希》。伍尔夫对传记的持续探索毫不令人意外,因为她的父亲可是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传记作家。父亲对她来说,是衡量的尺度,更是要超越的标杆,因此她的传记理论也和父亲的截然不同,戈登认为这里有她的真正创新之处。她想象的传记对象是那些仍在成长中、未成形的人物,她的传记想写的是人物的“暗”面,她认为传记不应该假装可以完整地定义一个人。
戈登为我们指出了这些,她自己的巧思,则是反过来用伍尔夫的小说方法来书写她本人的传记。戈登认为,伍尔夫的一大贡献,是强调了记忆和想象这两种脑力活动对人的重要性。也就是说,对于一个人来说,最重要的也许并不是标记时间节点的那些大事,而是某些瞬间,这些瞬间才是决定性的,再平淡无奇的瞬间都有可能激起饱含感情的回忆或天马行空的联想。戈登是这样来解释人们一般称为“意识流”的写作手法的,整部传记甚至一次也没有提到“意识流”这个词。她秉持同样的原则来书写伍尔夫的一生,即并不严格按照时序,而是选取她看到的存在的瞬间,从伍尔夫的小说随笔和日记书信两种书写里自由而合理地取材。我们不妨看她的自述:
这部传记标明了那些不与外部事件同步的转折点:1892年,一个十岁的孩子看到了父母不朽的品质;1897年,姐妹两人学着独自行走;1905年,这位年轻姑娘开拓了她的小说的非正统形式;1907年至1908年,她发现了记忆的作用;1912年至1915年,她克服了婚姻和精神上的种种困难,建立起自己的私人生活;1925年那个创造力丰沛的春天;1926年的“鱼鳍”;1932年“灵魂的变化”。她把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想象成一次探索之旅,甚至把衰老也看作一次冒险,正如她在1940年5月6日所说的:“就这样,我的船驶入老年的海洋,陆地退去了。”
这部伍尔夫传记最初出版于1984年,是林德尔·戈登的第一部女作家传记,2006年戈登对初版做了修订。此后在2017年,戈登出版了一部女作家集体传记,这本书的标题《破局者》,恰恰借自伍尔夫的一个说法,Outsider,也即局外人。伍尔夫自1932年起开始称自己局外人,并且说一个庞大的局外人群体已经存在,这些人就是薪资微薄、默默工作的数百万普通女性。《破局者》写了五位女作家:玛丽·雪莱、艾米莉·勃朗特、乔治·艾略特、奥利弗·施赖纳和伍尔夫。这五个人里,除了伍尔夫,其他人她都不曾写过单独的传记。回到伍尔夫也颇有深意,在《破局者》里,戈登是如此作结的:
1929年,弗吉尼亚·伍尔夫认为界定“女性真实的本质”是不可能的。她说,答案必须等到女性在政治和职业中得到检验后才能显现。然而即便是现在,在又过了一个世纪之后,答案仍然不确定。在我看来,这就是其中的原因:女性仍在寻找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、协和的声音。
这一点当然在《伍尔夫传》里也曾提到。戈登认为,伍尔夫本人就是处在未知地带边缘的实验性存在。伍尔夫的先觉,以及她勇猛进化的成长过程,是我们现在仍要去了解她的一生的意义。而除此以外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,要快乐!戈登打破了一个忧郁的伍尔夫的迷思。她的确患有精神疾病,但在她大部分健康的时间里,她自认为比百分之九十的人快乐。如果说广大的局外人群体仍有未完成的斗争,也请记得她的叮嘱:
保持耐心,保持愉悦。